
秦倩、徐以骅主编:《医学与国际关系》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
本书为《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第一本(第二本为专著,在出版流程中),亦是《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系列出版物之一。该系列已经出版29辑。本书为第23辑。本辑专题是“医学与国际关系”: 医学的全球化传播历史,凸显了医学与国际关系的复杂历史纠葛。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于2018年5月11-12日举行“医学与国际关系”国际会议。来自医学、国际关系、公共卫生、法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自由而有用、有趣的讨论,也由此激发并成就了本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的主题。应该说,围绕医学与国际关系,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有太多有待探索的领域与课题。

秦倩,法学博士、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杨百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上海浦江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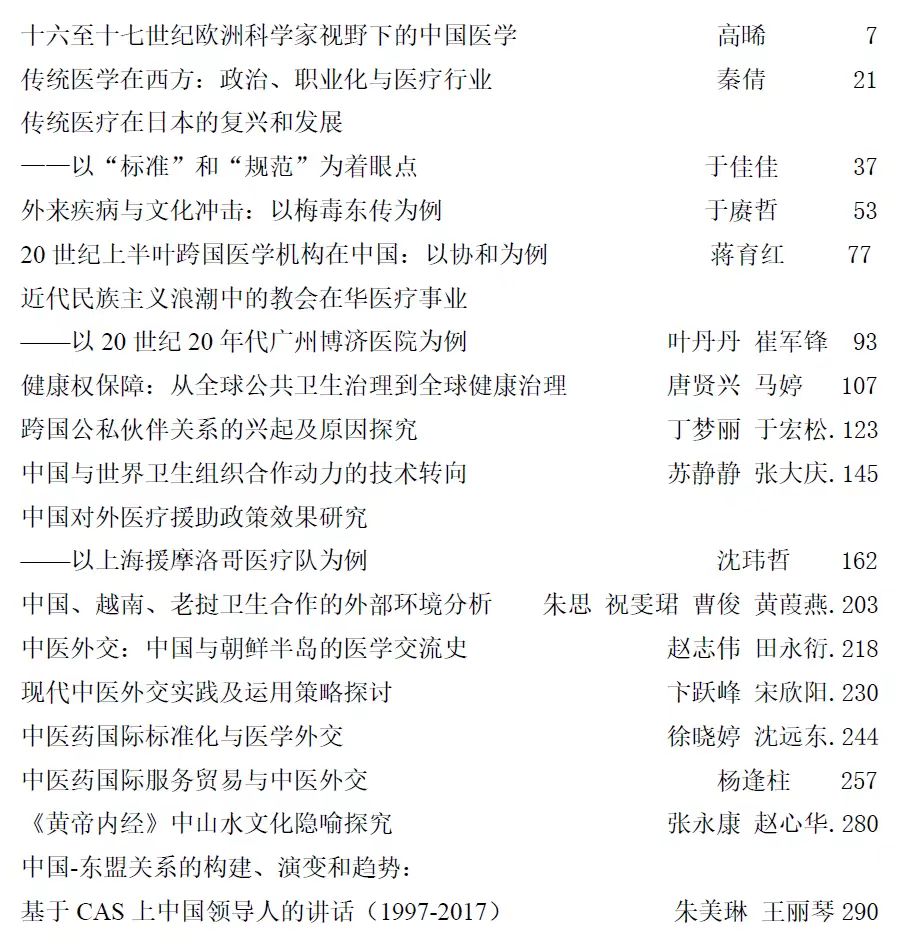
我们往往不能详尽的了解整个医学史,因为医学领域中疾病本身的概念相当复杂且令人费解,其确切定义不仅因时空变化而暗中偷换,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对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的认识,及其起因和意义均有不同的看法,经数千年时光的淘洗久受浸润至今仍然执守这种信念。古代用以预防病痛的信仰和实践出自于其特有的文化,并与民众信守的社会、道德和精神理念一脉传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这一概念涵盖范围广泛的各种地方性医学,这些地方性的治疗方法和实践在各国、各地区呈现不同的面貌,但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19世纪以后插上科学翅膀、重实证的现代西医学判然有别。
实际上,西医学最初也是一个地方性医学,而且与其他社会的民族医学相比,产生更晚。当漫长的中世纪(公元5-15世纪)时,欧洲受教会统治,基督教作为“神圣的帷幕”侵入并垄断社会关系,为包括疾病在内的一切领域提供解释。在天主教的大一统下,疾病被视为上帝对人的惩罚,治病疗伤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以天主教会禁止医学研究。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才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推动“人本主义”的兴起与科学的发展。1543年,维萨里出版《人体之构造》一书,为现代生物医学体系的初创奠定学术基石。17世纪科学进一步发展,启蒙运动使它广为传播。但此时科学对医学的影响与贡献尚微。时光的时针就这样匆匆指向了19世纪,直到这个世纪才是真正的科学时代,西方各大国和各个大学系统性的奖励科学进步和设立科学基金,才使医学和科学紧密结合起来,促使现代西方医学高歌猛进。科学不断向医学领域渗透,细胞病理学说及细菌学的发展对疾病原因提供了更准确的说明,化学研究带来了麻醉药和消毒剂的发明,使得外科手术成为西医的强项,手术所依托的医院开始彻底的现代转制。同时,药理学的发展推动了制药业的进步,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以及一系列光学器械的应用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至今仍在刊行的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Lancet)也在1823 年问世。这些合力促使科学医学的体系形成。
19世纪,西医学完成其科学化、系统化之后,随着西方殖民统治与海外贸易、以及基督教传教的带动下,也日趋全球化。诸如早期的英国、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美国等在本土之外谋求军事、经济或势力扩张的国家,无一不关心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流行疾病的影响范围,唯恐这些“热带疾病”害及本国在外的政客、商人和教士。因此,像东印度公司一直设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医疗机构,当英国殖民政府镇压了1857-1858年印度反英暴动(the Indian Mutiny)从而牢固控制印度后,该机构转型为印度医疗服务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西医”(WesternMedicine)相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的传统医学始终保持高度优越感,一些按西医思路设计的医学院和医院得以建立并旨在培养当地居民。而传教士们在东向禾场的时候,随身携带的除了圣经还有药品甚至显微镜。这些西医传教士初履东土就承担着“宗教”(基督教)与“科学”(医学)两种职能,负有双重的教化使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20世纪初期,“宗教”与“科学”双重功能中宗教成分在消退,科学层面却在不断凸显,由此在东方社会创造出了一个“现代医疗殖民”(imperial medicine)的新空间。
换言之,西方医学的传播与西方现代帝国勾画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规模扩张的路线图之间构成了相互对应关系,这使得原本局限于西方一隅的西医学被持续的输入非西方地区,“欧风美雨,驰而逐东”,冲击并取代各地方性医学,不但建立科学医学的权威地位,全球同此凉热,也因此对世界医学格局及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波西潮挟其威势卷地而来的情况下,出现了跨文化语境下不同医学的对峙。我们知道,医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它所受到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要比自然科学大得多,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时被地理环境、社会伦理、文化价值取向等人文因素影响与塑造,由此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疾病认知与治疗实践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在疾病认知上,一种文化中的疾病在另一些文化中可能不被认为是疾病,甚至被视为健康的表现。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文化都不把肠道寄生虫看成是疾病,只有当寄生虫引起呕吐、窒息或其他不适时,才需要由医生予以治疗。
在疾病的认知基础上,很多社会关于疾病的发病学原理也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学就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建立了自身的病因学理论,认为外邪、七情、饮食劳倦诸事都会成为危害人体的致病因素,而先天因素、外伤及寄生虫等也可能是疾病的原因。在《内经》之下,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将病因分为内所因、外皮肤所中和房事、金刃、虫兽所伤三大类,成为《内经》病因理论之补充。在此基础上,后来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论”:“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
显然,中医学除了关注外邪,还把疾病归因于人体正气或情绪的作用,并在病因学解释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相应的疾病预防与治疗体系,这一点与西医学迥然不同,呈现出巨大的跨文化差异。
在跨文化背景下,不同地方性医学各有特色是不言而喻的。新大陆发现后的很长时间内,西方人也承认这一文化差异的存在。当欧洲人看到亚洲的草药治疗、印第安人的萨满仪式等,凡此种种皆与自己当时所持的以体液病理学为主的疾病观完全两异,但也尊重这样一种治疗实践,尚未别尊卑、分贵贱。比如,明末清初早期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对中国医学就有臧有否。他们对中国医术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精细的把脉诊断方法。除了西来的传教士,那些浮海东来的西方医生和博物学家也关注中医典籍的翻译。德国人克莱叶(Andreas Cleyer)作为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医生,1682年曾出版译著《中国临床》,书中节选了《王叔和脉诀》、《脉经》、《难经》和《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英国医生福劳业(John Floyer)正是受此书启发,发展出一种结合西方和中国诊脉经验的诊断新方法。大致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和受其影响的西方人还是乐于向中医学习的。
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细菌学在欧洲医学上的成功,以及传教士所持的“文化沙文主义观”,后来者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医学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巫术”,甚至可与星相巫祝之流的“迷信”事务并列,西医与传统医学的对比被转换成新与旧、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落后的对立。西方的生物医学挟其话语霸权随着西方殖民统治者和传教士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西方人,这些东迁的西方人先是在北美大陆、澳洲等地,比照本国模式建立起新社会,西医体制也随之移植过来,本土医学的存在空间愈益局促竭蹶。之后欧洲殖民者的风尘足迹更深入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地区,传教行医将治疗躯体疾病与拯救灵魂绾和在一起,教堂与教会医院便成为西方文化在非西方国家的标志。这一过程,梁启超曾语之“莽莽欧风卷亚雨”,可谓描画都尽。
西医的这种“政治正确性”,不仅为西方人所簇拥,甚至支配着很多急欲摆脱殖民和半殖民不堪境遇的东方社会。比如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下,时人多指责中医缺乏“近代政治理念”,不但不能成为救治社会病症的“社会医学”,也有碍科学与民主的传播。按余岩的说法就是:“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3这种从笔底泻出来的文字反衬出时人的忧怖交集,似乎中医与西医,不仅关乎“迷信”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也是“亡国”与“救国”的政治分水岭。因此,对志在收拾时局的人来说,中医必然成为被剪芟的对象,由此而有1929年的第一次“废止中医案”。中医的“存”与“废”,表面上围绕中西医理的分歧争议,中医是“玄学”还是“科学”等等。但其底里毋宁是,“中医”与“西医”、“旧医”与“新医”的核心区别乃在于是否拥有完备的“卫生行政”能力,而总是以分散状态面对病人个体的中医,根本达不到“强种优生”的现代政治目的,换言之,中医不能为现代政治所用。中国的现代政治由是选择在西医的基础上搭建了卫生行政制度,而国家在医疗行政上的现代设计蓝图可以说完全出自西医手笔。在西医的这一天罗罩下,中医成为屡遭摧锄的对象,转为国家现代卫生权力结构中奄奄无气的一方。其自救、其抗辩、其谋求合法化的种种努力,都很难逃脱中医传统被全盘置于西医控制之下的命运。
这一命运不惟中国的传统医学所是。对于同时期获得殖民独立的新国家之传统医学,大体都经历了类似的丕变。一来,这些新获独立的国家,要“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往往选择复刻西方经验,建立以西医的行政化形式配合以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垄断的现代卫生制度;二来,即便这一卫生行政制度不是自发选择,到了二战结束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启动的发展援助计划也附加了援助条件,要求获得殖民独立的新国家建立系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之后的半个多世纪,西方生物医学进入并取代地方性医学成为医学跨文化传播的主旋律。在全球医学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生物医学劲气辐辏,风气播染之下被视为普适性医学,由此贴上现代性与进步的标签,拥有“政治正确性”,成为发展中国家落力追蹑的对象,以生物医学为圭皋,引导本国医学走向药物生产工业化与医疗保健生物医学化。而以此律彼,在相当多的后发国家,生物医学之外的地方性医学被普遍认为仅具文化研究的价值,临床应用意义较少。各种传统的地方性医学作为生物医学的“替代”或“补充”,只在极少的场合使用。
时势比人强,在二战结束后的20余年间,国际社会新生国家大多自上而下建立了西化的现代医疗卫生体制。但这一现代的医疗服务体系,或者说医学-工业复合体,往往需要精心设计的临床试验、庞大的医疗辅助机构以及大量的药物供应,这一切无不意味着高昂的医疗费用。而对于刚获政治独立的国家来说,经济水平普遍低下,高昂的医疗费用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卫生体制支持下的西医短时间难以惠及社会的大多数人口。于是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增加医药的可及性(access)成为最迫切的使命。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二战后的30年,高科技医学的发展使得可应用的医学手段大大丰富,但医疗费用和医疗开销也急剧膨胀,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美各国普遍都在寻找限制医疗费用的方法,可以说,决定西方世界下一时期医学政策的关键,是高科技医学的费用问题。2而在社会层面,医学反文化(medical counter-culture)思潮的兴起和涌荡也使得科学医学的机构和权力都受到了攻击。
因此,无论在先进还是后进社会,西医在现代卫生体制中的垄断地位都没能彻底吞噬传统医学的存在和力量。在不同社会,于是逐渐生发出“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新医与旧医、西医与传统医学的“反复”和“羼杂”浮现在不同国家的社会土壤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医学的山重水复。由此,我们可以说医学的全球化传播历史,凸显了医学与国际关系的复杂历史纠葛。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于2017年11月17-18日召开“医学与中国外交”学术会议,以及2018年5月11-12日举行“医学与国际关系”国际会议。两次会上,来自医学、国际关系、公共卫生、法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自由而有用、有趣的讨论,也由此激发并成就了这期《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的主题。应该说,围绕医学与国际关系,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有太多有待探索的领域与课题。
本辑的出版和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除了所刊论文专门论及之外,还得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资助。对上述单位和项目资助方,本刊编辑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略)
秦倩
2018年9月15日


